中医与神经网络
几天前的某一个早上,当我像往常一样打开QQ时,突然看到一位群友发来了一张截图,并且将其评价为“神人”。我点开图片,然后真的看到了一位自学成才,靠中医来“预防疾病”的“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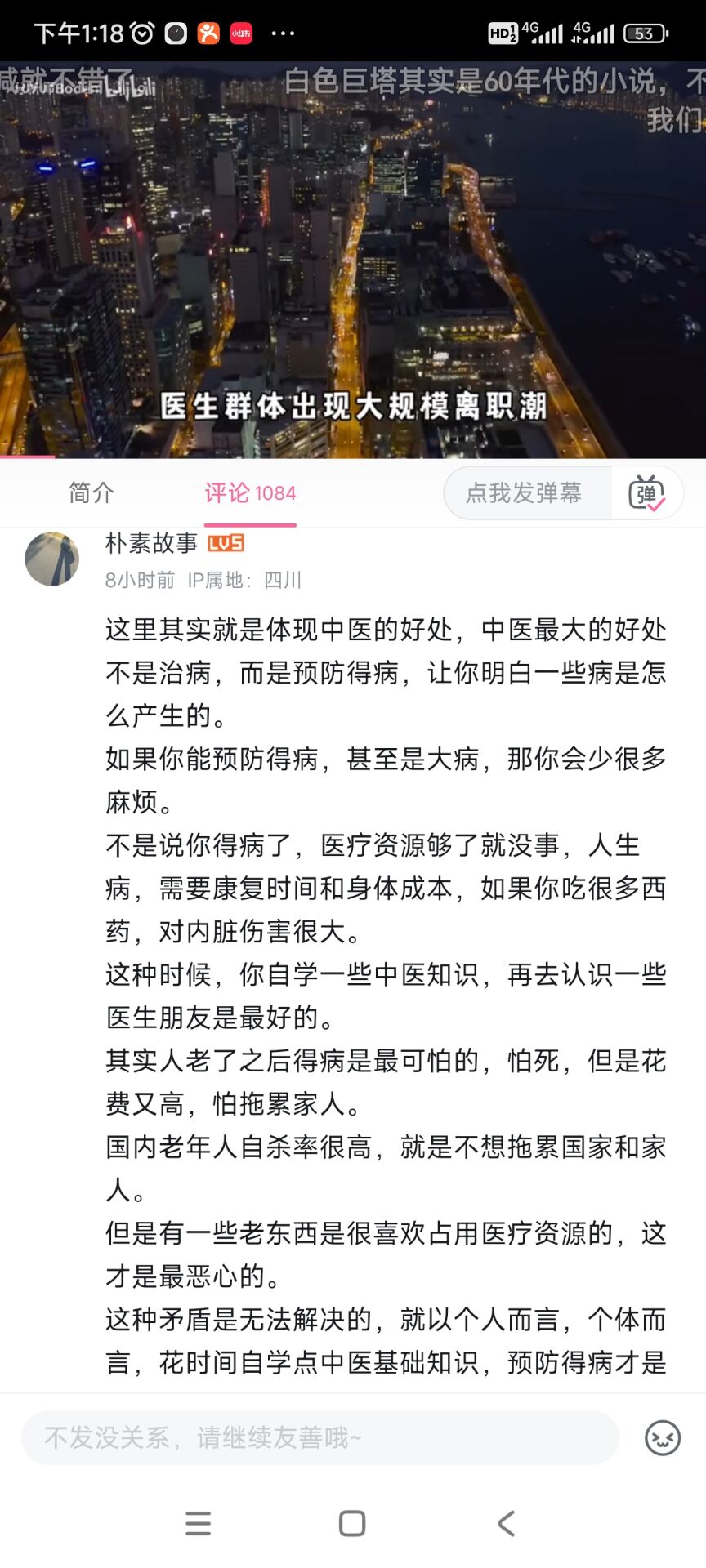
作为一位医学生,这位群友平时就喜欢在群里讨论生物医学相关的话题,并且尤其反对中医。我本人对中医的态度虽然并没有这么极端,但对图中这位“神人”的言论也确实难以苟同,尤其是那句“西药伤害内脏”,也确实符合那些完全没学过生物的人脑补出的刻板印象。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西药伤x”的说法恰恰反映了它们在药理学和毒理学方面的研究已经非常完善,副作用已经通过大量临床研究和长期观察得到了充分验证。退一步说,能够清楚地知道哪些药可能对什么内脏造成损伤,就至少能在事先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预防和监控。而中药呢?随便打开一个药物说明书,我们看到的通常是各种“副作用尚不明确”,鬼知道吃了这些东西会产生什么危害。
对于中医的理论体系,其实我也一直持怀疑态度。我实在很难想象在科技已经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会有一大群神人抱着公元前3世纪提出的阴阳五行学说,把古人臆想出的五大元素往人体五脏上生搬硬套——毕竟在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由希波克拉底提出的类似的四色体液论,早就被后来发展起来的解剖学和生理学完全推翻了。就算是目前同样还在使用这套阴阳五行理论的所谓“风水学”,也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现代心理学的影响,虽然名义上仍在研究厕所的位置、镜子的摆放之类的玄学问题,但其核心思想早已从传统的灵异鬼怪故事转向了对心理暗示和环境对人类行为影响的研究。
然而存在即为合理。中医那些狗屁不同的理论能够流传至今,必然说明它在某些层面上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实际效果——毕竟一代又一代的中医传人们不太可能全是傻子。因此,中医能够跨越两千多年的历史而没有失传,证明它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能够解决患者的健康问题。尽管在前文中我已经对中医理论放了不少黑屁,但我也确实无法否定其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已经被现代医学宣判死刑的情况下)治愈患者的能力。作为一门经验科学,我相信每一个中药方子都至少曾在某个患者身上起过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问题在于,我们永远也无法确定,这些成功的案例究竟是因为药物本身的真正疗效,还是单纯依赖于安慰剂效应或是别的什么偶然因素。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正是在这种不确定性中,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得以传承下来。因此我认为,“中医”这个词实际上指代的并不是特定的某些药,某些药方或是某些阴阳五行理论,而是一种传统的、朴素的、形而上的研究方法,是古代人在缺乏现代科学理论指导下的一种试图通过观察自然、模拟规律来解释和干预人体的尝试。
这种推理过程充满“黑箱”,却常常能够得出惊人准确结果的特性也确实让我再一次联想到了神经网络。可以这样说,中医就像是在计算机尚未发明的年代,人类用无数代人的无数个大脑作为GPU训练出来的,结构不算复杂但还算是实用的人工神经网络。这个“真·神经网络”以无数患者的具有个体差异和随机性的数据作为训练样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通过一代代医生(郎中?)的不断试错和验证,最终以药典的形式传输和记录下来。而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出,由各种草药混合而成的“大锅生物碱乱炖”也确实有其独到之处。作为植物在与动物的漫长军备竞赛中研发出的化学武器,很多生物碱复杂的结构和独特的生物活性确实让它们有潜力成为潜在的药物。例如,单就乙酰胆碱这一种受体来说,就有尼古丁可以精准地激活n型受体,而东莨菪碱则可以通过拮抗m型受体发挥作用。虽然古人并不懂分子生物学,但他们通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和试错,逐渐发现了这些草药在调节人体的某些生理过程中的某些效果。
只不过,受限于人脑的想象力和古代科技水平,中医的发展也就只能停留在这一高度上了。如果按照几百甚至上千年前的标准来评价,那么能够整出一套完整的方法论,在当时确实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了。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你不能把几百几千年前的“先进”还当做是现在的“先进”,死死抱住不放。这就好像我特别讨厌的那些网络小说里,主角总是靠“考古式修炼”,挖掘越古老的东西,——比如什么“上古遗址”里的功法,反而能比现代科技更牛逼。而如今的中医,恰恰就是走入了这种“考古式研究”的窠臼中,总是试图从古籍、从那些曾被归纳为经验的文本里寻找新的突破口,却忽略了这些方法和理论是基于几百年前的认知框架建立的。在现代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继续用古人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未免显得步履蹒跚。
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日本药学家长井长义在美国的实验室里首次从麻黄草中结晶出了麻黄碱;1913年,在长井长义分离出麻黄碱30年后,久保田等日本科学家又对麻黄碱进行了进一步研究,重新审视了其药理作用。他们发现,麻黄碱是一种拟交感神经药物,可以通过激活交感神经系统来起效,从而有效治疗如哮喘、鼻塞等一系列与气道收缩相关的疾病。在我看来,这一系列研究才算是真正开创了中医现代化的先河,也是迄今为止中医药研究中最为正确的方向之一。长井长义等人没有执着于传统理论中的阴阳五行、气血虚实,而是利用现代科学的工具和方法,从中药中提取活性成分,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开始研究它们的结构和具体的生物作用机制。在我看来,正是这一发现让麻黄草从“中药经典”摇身一变成为了“现代药物”,走进了千家万户的各种感冒药当中,也让中医从“经验科学”向“实证科学”迈出了关键一步。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万一所谓的“分子生物学”其实也是错的呢?假如未来的科学家站在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技术高度,再回头来看今天的分子生物学时,会不会就像我们今天看待阴阳五行那样,认为它也只是一种基于当时认知水平的“过时理论”呢?这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法想象的,毕竟历史上许多曾经被认为是“科学真理”的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都曾被推翻过。从地心说到血液循环,再到量子力学的诞生,科学的历史总是充满了不断的自我革新与自我纠错的过程。被今天的我们所奉为圭臬的分子生物学,尽管在现阶段能够提供有效的医学和生物学解释,但它毕竟还是基于21世纪的科技工具和观念。如果未来的科技进步能够让我们对生命的理解进入一个全新的维度,那么今天的分子生物学理论,或许也会变成另一种“中医”。
从马哲的角度来看,科学是一种不断接近真相的过程,而不是追求最终的、绝对的答案。因此科学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断的实践、修正和积累中前进的。每一阶段的科学理论都是基于当时的认知和技术水平,在其局限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新的发现和技术进步,旧的理论会被修正或替代,这本就是科学进步的常态。然而,现在的有些傻B中医却完全无视了这一点,仍然在研究阿司匹林是性热还是性寒。对此我只能说,虽然阿斯匹林是人工合成的,是西药,但这种研究仍然是傻B中医,他们的科学观反而不如清光绪十三年的长井长义了。